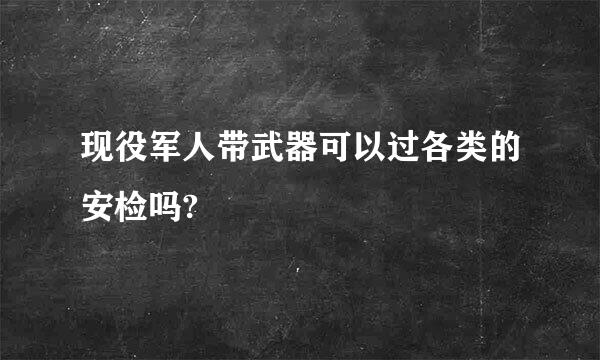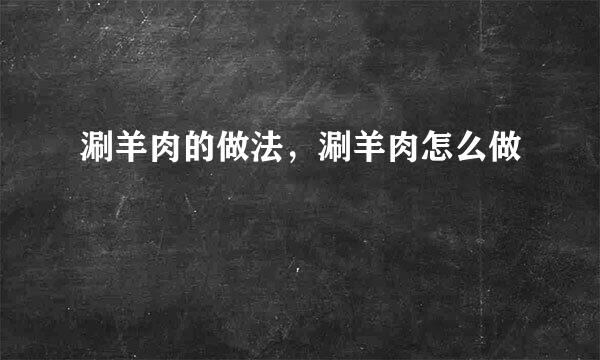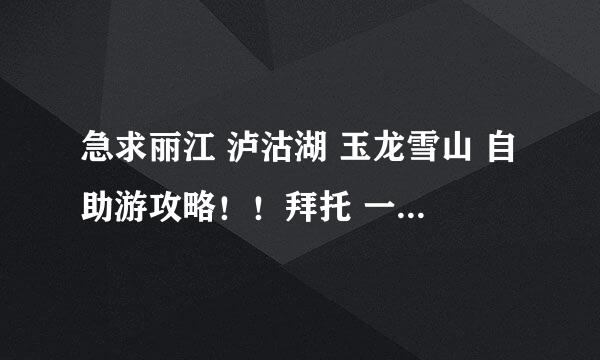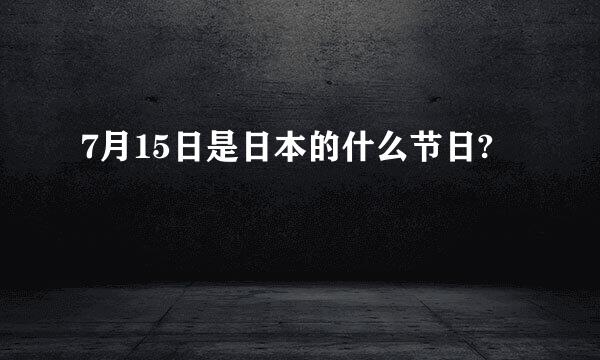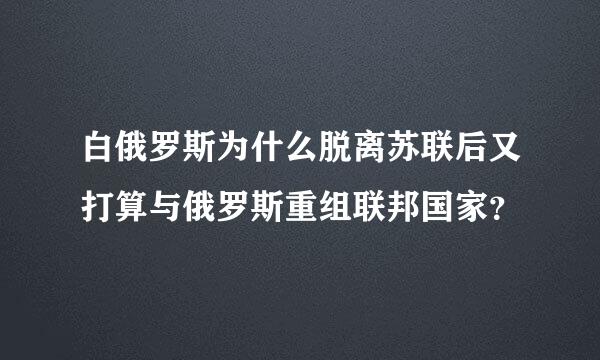现代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无所不在,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意义生产这一领域,广告不仅仅“广而告之”产品与服务,还在指引人们购物的同时输出某些观念,给人们以意义,给人们以种种美梦和由这些美梦所标识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速成某些惯例,把消费者纳入这一“意义”框架。换言之,广告首先推介和生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时获得的实际利益,还包括他们同时获得的某种“精神享受”,并把这种双重满足或通过广告词直接言说,或通过营造氛围实现 “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通过把受众建构为广告主体,使创设的某种观念化的说辞和极具诱惑力的意象推广到大众中去,竭力使之成为大众的利益和观念,在此广告完成了它的意识的制造和传播。当这一观念或意象成为大众或某一群体的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或意象时,意识形态便发生了。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 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 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 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 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 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 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 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 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 “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 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标签:广告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