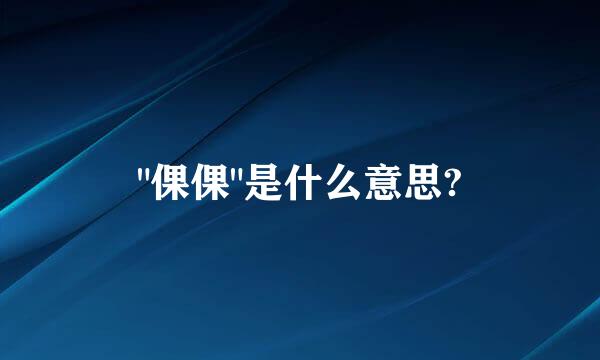“新帝国主义”是当前国际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它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或新阶段。毋庸置疑, “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属于高频率使用的流行词汇,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其内涵又一向具有丰富、变动的特点,然而越是如此,概念也就变得越不确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冷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研究中,也体现在今天泛滥如觞的种种 “新帝国主义”论中。因此,挖掘 “帝国主义”多元表述背后存在的问题,继而把握住变动中的概念的本质,不仅对于理解整个帝国主义理论史非常必要,更是理解今天的新帝国主义问题所迫切需要的。一、当代帝国主义研究中的混沌问题在国际左翼学术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一个观点:所谓新的帝国主义与二战前的古典帝国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即新帝国主义不再追求表现为领土兼并和殖民征服的直接政治统治,而是注重经济控制的作用,但围绕 “新帝国主义”依然有诸多争论和分歧,其中暴露出的最主要问题是,“新帝国主义”的指向并不很明确。首先,国际左翼在 “何为新帝国主义”者尘上认识并不统一。有的学者把新帝国主义看作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强调二战后或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还有的专指新世纪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径。其次,即便是同一个作者,对新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它时而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时而又是一套 (政治或经济的、或二者兼有的)权力机制,时而被当做一种行为模式,时而又被说成一种政策。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许多国际左翼学者并没有很好地说明新帝国主义与当代战争、军国主义的具体关系。进入新千年以来的所谓美国反恐战争正是促成 “新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产生,并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左翼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氏拆的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张性,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旧帝国主义战争的简单复归?既然殖民征服已不再是新帝国主义的特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军事行动体现的暴力征服究竟是帝国主义的附带结果还是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系到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自洽和现实说服力。然而许多作者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恰恰是语焉不详的,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中尤为常见。例如,美国 《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 “帝国主义”是用来揭露和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术语,因此,他把 “新帝国主义”叫做 “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在其他左翼经济学者的论述中, “新帝国主义”也常常作为 “全球跨国垄断资本权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或者 “美国金融霸权”等诸如此类与经济霸权相联系的概念的同义语出现。在这些学者看来,新帝国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他们对战争等超经济暴力形式的独特意义基本缺乏足够的或独立的分析;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霸权和战争首核禅行为又往往构成他们关于 “新美帝国主义”命题的重要内容和论证归宿,这就形成了一定的逻辑矛盾,同时也造成在 “新美帝国主义”概念的指向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与美国军事霸权的话语往往不同程度地混杂在一起。福斯特也经常将 “帝国主义政策”与 “垄断资本扩张”、“军国主义”等术语混用,但是,很明显,这些概念并不能直接等同。概念运用和议题的混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不少左翼在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以及 “新帝国主义”理论所蕴含的问题核心上缺乏明晰的意识。综上来看,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研究方法 (借用阿格列塔的话)具有浓厚的经济还原论色彩,在此分析框架中,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来源于第二国际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因为后者把帝国主义的根源完全归结为资本积累特性。然而,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前提的。与 “新帝国主义”的议题相比,一战前后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无论是 “帝国主义”所指对象,还是帝国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都很明确,那就是,如何看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剧的西方列强对外抢占殖民地和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 (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此外,即便是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在从经济方面来解释帝国主义的根源和本质上,也并非无懈可击。卢森堡的帝国主义论以资本主义再生产不能自我实现的消费不足论为前提,但这一点已遭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诸多有力质疑,因而日益被削弱了。考茨基从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出发来解释帝国主义,也早就受到列宁的驳斥。列宁正确地指出他立论的错误:帝国主义不只发生在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工业国之间。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竞争间矛盾的产物,但是,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导致的冲突,并不必然要以战争的极端形式来解决,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来说更是毋庸置疑的。希法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中,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资本输出的不同形式恰恰表明,并不是对一切外部区域的投资都能产生扩张领土的动机,只有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区和 “无人认领区”,才引起了以暴力来实现投资利益的需要。同样,列宁在强调对外 (政治经济)扩张是垄断资本的根本要求时,又区分了垄断资本在美洲等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地区和亚非拉等资本主义不发展地区的不同统治方式,因而也无意中区分了殖民地的两种形式:经济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经济殖民地,即非暴力统治的经济附庸,正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统治的主要类型,这反而说明了经济上的控制和垄断并不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控制和垄断。以上表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完全从那一时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寻找帝国主义的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就此需要再次明确,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到资本积累过程中去寻找的,不是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帝国主义的根源,不过,他们通过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必然产物的论述路径,将原先表现为殖民征服与列强争霸战争的帝国主义议题,转换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议题。例如,当列宁把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时,他实际上是以 “垄断资本主义必定导致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为前提假设的。但问题就在于,沿用列宁帝国主义论断的当代理论家们却摈弃了这个前提,承认在当代殖民主义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并非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在他们那里,一方面, “帝国主义”成了一个包罗资本主义万象的含混术语;另一方面,继续借用古典理论指向领土垄断的分析思路来解释当代 “非领土垄断的军事冲突”的实质,这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矛盾,反而在理论上更加削弱资本积累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这二者间的逻辑联系,使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更加模糊。二、两种积累逻辑:对概念内涵和问题意识的廓清对于 “帝国主义”与 “新帝国主义”内涵不清 问 题,加 拿 大 学 者 利 奥 · 帕 尼 奇 (LeoPanitch)和萨姆 · 金丁 (Sam Gindin)较为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提出要从概念上区分 “资本主义”与 “帝国主义”,认为不能直接把 “帝国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混淆二者的范畴。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生产关系的领域,帝国主义则与国家行为或国家关系相关,二者分别属于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范畴。不过,尽管帕尼奇和金丁严格限制了 “帝国主义”的领域,他们对新美帝国主义本质的阐释照样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囊括了进去,同时却没有指明 “资本主义”与 “帝国主义”这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世界体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乔瓦尼·阿锐基 (Giovanni Arrighi)较早注意到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帝国主义几何学》一书中,他通过对比和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扩张模式指出,由霍布森开创、并由列宁极大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的内在动力都是各不相同的。阿锐基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解释路径。他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引入了 “霸权”的概念,用以替代 “帝国主义”的概念。在阿锐基那里, “霸权”似乎是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含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又体现了权力的强制和认同的结合,它只指向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即霸权国家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有多个)。沿着同一思路,阿锐基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期霸权的不同特征,并揭示霸权背后实际上存在两种权力逻辑: “领土阶级统治”(territorialism)的权力逻辑和 “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前者的根本目的是取得领土,后者则追求利润 (货币资本)。两种权力逻辑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组合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不同的帝国主义模式。阿锐基的分析方法其实并非独一无二,在许多具有历史敏锐性的作者那里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结论。早在考茨基分析帝国主义时,他就已经指出,国家对外扩张虽然必须以经济条件为依据,但并不是每次扩张都出于直接的经济要求。概括地说,国家扩张背后有两种动机:一种是工业资本主义兼并农业区的经济动机 (他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动机”),它只是19世纪末新出现的扩张倾向;另一种则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更为原始的动机,即单纯依靠暴力来占有领土和勒索贡品,实施直接政治统治,它仍然构成19世纪末以来的殖民主义的重要内容。考茨基的这一论述通常是为人们所忽略的。也正基于此,他才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可采取的其中一种政策,因而,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同样区分了帝国主义中所包含的 “权力积累”和 “资本积累”的不同方式。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对新帝国主义的阐释则深受阿伦特和阿锐基的启发,他也提出 “权力的领土逻辑”和 “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概念,认为前者代表国家战略对领土 (空间)控制的要求,其手段是超经济的强制,后者则是资本积累的要求,其手段是经济强制,帝国主义正是反映了同一积累过程中这二者间的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得不说,阿锐基等人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拓宽和提升了我们把握帝国主义的视角,也深化了我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解。总结起来就是,他们都区分出了私有制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并列的财富积累方式——超经济强制 (与哈维的术语“剥夺性积累”类似,但又不完全一致)与经济强制 (“强制”在阿锐基那里,又必须同时带有“认同”的意味)。超经济强制的主要实施主体是国家,它表现为通过战争等暴力征服手段来获取国家政治霸权,是前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而经济强制反映的是资本的权力,它表现为单纯的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又可称为资本积累的逻辑。这两种积累逻辑虽然具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独立性,因而,两种可能的积累要求的差异及其辩证关系是构成霸权扩张、帝国主义行为的动力和基础。从这种理论视角来看,古典帝国主义中所包含的领土兼并式的积累具有其内在相对独立的逻辑,并不必然和完全被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战前的帝国主义行为中,殖民征服与资本剥削的对象并非总是一致,且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方式存在差异。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帕尼奇和金丁把 “帝国主义”仅仅划入政治的范畴是片面的,这一判断也与后面他们的理论展开逻辑相矛盾。当帕尼奇和金丁批判新帝国主义时,他们同样不得不借助大量的经济分析,通过资本积累的演变方式来论证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并用 “美帝国”这个综合性概念来作为新帝国主义的现实范本。(包括 “新帝国主义”在内的) “帝国主义” (正如阿锐基的 “霸权”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同时包含了压迫性的军事暴力征服和资本积累霸权这两个方面,表现为霸权力量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关于这一点,哈维也明确表示,在对帝国主义做具体分析时,应避免落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模式。无独有偶,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两种形式的交叉和融合,构成了 “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这两种形式的关系。三、两种积累逻辑关系的演变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是,即便指明了作为帝国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两种积累逻辑,对于另一同样重要的问题——两种积累逻辑之间关系的运动发展轨迹和方向,阿锐基和哈维等人却还没有足够清楚地加以阐释,而这恰恰是阐明从古典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发展根源的关键所在。尽管阿锐基指出,每一次世界体系积累周期更替 (同时也是霸权的更替)的动因在于,新的霸权的积累体系具有优于前一轮的霸权积累体系的特点,但是我们从中并不十分确切地了解,为何在英国霸权身上,“领主阶级的权力逻辑”体现较强,而到美国霸权,“领主阶级的权力逻辑”体现较弱,且 “资本的权力逻辑”成为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积累逻辑?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则从一开始就设定国家权力及其积累逻辑处于资本积累逻辑的从属地位,也没有涉及二者关系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哈维并没有明确区分所谓的领土 (空间)控制与领土的直接控制,在他看来, “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一直存在于新帝国主义中的。相反,从埃伦·伍德 (Allen Wood)具有强烈历史感的著作 《资本的帝国》那里,我们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古代的帝国模式到当代的美帝国主义,经济强制是如何逐渐取代超经济强制成为帝国可靠的统治工具的。伍德首先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与资本的帝国 (这种区分在阿锐基的霸权周期论中并不明显)。她指出,古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作为以掠夺领土、聚敛资源为目标的 “领土的帝国”,中华帝国作为压制大地主阶级、依靠庞大的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共和国作为致力于夺取国际贸易控制权的 “商业帝国”,无论它们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过直接的暴力胁迫占有财富,实行超经济统治。前资本主义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因而生产者、剥削者不存在市场依赖现象,军事、政治强制与经济强制来自同一根源。到了16世纪的英国,由于领主们采用竞争性的土地租赁制度,经济法则开始成为剥削的手段,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出现。但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仍然通过暴力实施领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模式共同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超经济强制向经济法则过渡的时期。只有到了二战后,才最终确立了资本的帝国,即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沃勒斯坦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做了类似的阐释。他揭示,古代帝国体系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 (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两种具有不同的剩余攫取方式的世界体系。帝国体系建立于以暴力胁迫来占有剩余的政治集权化基础之上,世界经济体系则通过生产机制、世界市场来获取剩余。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帝国体系随着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被世界经济体系所代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政治力量不再作为中央经济的体现,它被用来保证资本的垄断权利。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出几点关于帝国主义 (以及新帝国主义)的结论:1.帝国主义作为霸权国家经济统治权力与政治统治权力的结合点,其本质涉及两种权力(作为两种积累逻辑的外在表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变化。2.两种权力关系的发展变化又是以社会的一定经济关系,及其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暴力强制和胁迫维持的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国家的暴力统治与经济剥削都来自于同一根源,即来自于专制君主(或封建领主)。对人口和领土的占有就成为统治阶级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即便商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专制权力的对外扩张就表现为领土兼并和对人身的直接控制等超经济强制的财富掠夺,也即暴力征服,正如阿瑞吉所说的,它体现了 “领主阶级的积累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经济从政治力量中逐渐独立出来,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的直接来源也分开了。政治统治权力来源于国家及其统治者,而经济统治权力来源于生产和交换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追求抽象的价值增殖,它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控制(例如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专业化、促进流通)就能实现这一点。因而,资本主义越发达,控制人身和吞并领土就越不必要,相应地,前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的积累逻辑和积累方式就越遭到削弱。3.古典帝国主义混杂着两种积累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实际上有两种方式,既存在领土兼并和维持殖民地封建剥削制度的超经济强制,又存在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等的经济强制,并且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两种积累方式的采用有所侧重。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英国帝国主义是两种方式并存,它在殖民地非洲和印度主要采用超经济强制,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地则采用经济强制。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虽然已经基本占主导,但在上层统治结构中,专制权力还未完全被消除;而在外部,其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并未建立,从而经济剥削的资本积累逻辑对其无法起有效作用,所以,英国对外扩张带有较强的前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积累逻辑色彩。葡萄牙、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同样是老牌的殖民帝国,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时还未占主导,政治统治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因而对外主要采取的是领土扩张的超经济强制方式。由于美国没有经过封建主义,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内完全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对外虽然也有抢占菲律宾等少数殖民地的超经济强制的一面,但主要还是通过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剥削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尽管资本积累与专制权力的积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资本积累本质上趋向于自由流动、同一,而专制权力的积累趋向于分隔和割据,但在当时的现实积累过程中,资本与专制权力却相互结合起来,并彼此利用:在首先分割式的占领中,资本借助着专制权力的暴力机器来为它的市场开辟道路,从而不断扩大积累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又为专制权力巩固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提供有力的物质工具。但是,既然专制权力的暴力征服 (超经济强制)还作为一种独立的积累方式存在,既然资本积累还不得不与专制权力的积累相结合,也就证明:在那一历史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还未达到它的高度发展。相反,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取得统治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在争取统治权,而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前资本主义制度或逐渐处于瓦解中或稳固未动。阿伦特恰如其分地指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 “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二战后才进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无论在全球经济秩序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首要维护者,因而,美国霸权通常被看作是新帝国主义的典型 (但不应是唯一的)范本,或某种程度上的同义语。正是在该历史阶段,两种积累逻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的权力 (经济强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世界扩张主导的积累逻辑,暴力征服则随着专制权力在其内部的消亡,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积累方式,而是退到了单纯的上层建筑领域,超经济强制也就不再表现为一种积累逻辑了,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的当代帝国主义并不以对领土的兼并和人身的直接统治为目标。在此意义上,暴力的实施者——国家变成了 “完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权力的发挥,包括国家战略的确立、军事力量的运用,尽管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最终是为资本积累服务,服从于国家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的。另一方面,在资本权力的逻辑主导下,资本的积累仍然离不开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需要在内部和外部都形成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阶级关系,这就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提供军事和政治力量保障:在国内,国家必须强行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并镇压威胁到资本积累秩序的阶级反抗;在国际,大国必须对落后国家实行地缘政治的控制,并对竞争者建立一种军事威慑力,以开辟和维护大国资本的海外利益。这样,超经济强制就与经济强制一起,共同构成了二战后霸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实现全球统治的两种并列手段,经济强制是其中的主要手段,超经济强制是辅助手段,因此后者的运用并不总是频繁和直接的。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扩张尤为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的关系、战争等军事暴力行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地位和性质的改变,正是体现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正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意义上,与彻底批判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对经济根本性的强调,以及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在所谓的 “新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具有继承与发展的价值
标签:动机,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