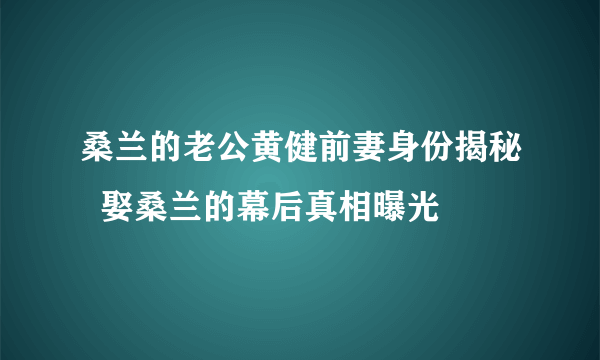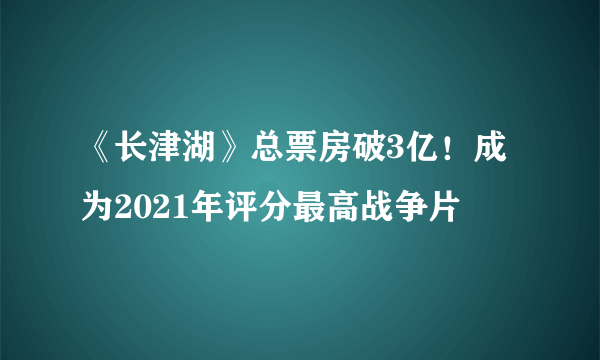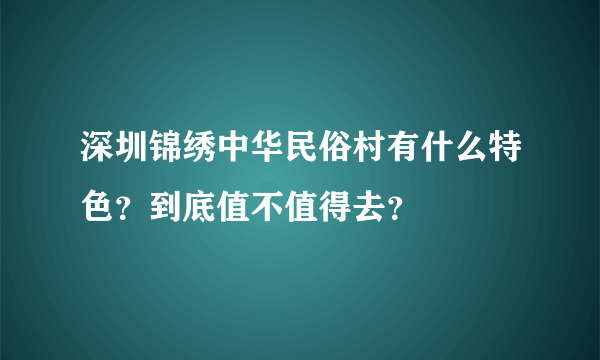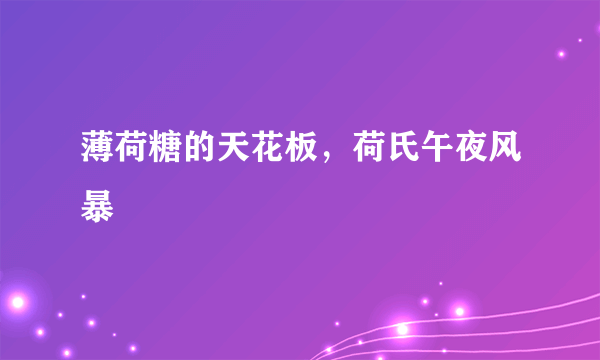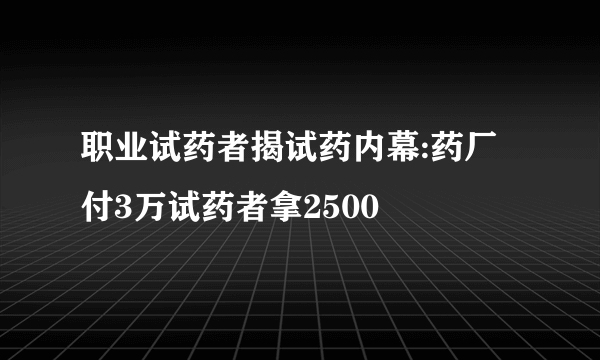
职业试药者
职业药品试验者生存录
“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元。”
好多年前,当中学生周飞看到Discovery频道那个关于药品人体试验的节目时,根本没想到自己后来会以此为生。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参加了20多次药品试验,拿到了大约4万元报酬。
周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陪朋友买到了自己曾经试验过的药品。此时,他特别强调自己的成就感:“不仅仅是拿钱做试验,也是为社会作贡献。”
当然,他知道这种成就感只能藏在心里,并不能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职业受试者---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默默关注着研究机构的受试者招募信息,然后穿梭于医院,体检、吞下药片或者接受注射,最后拿走或多或少的试验补偿费。
一个未经证实但流传广泛的数据是,每年中国约有50万人接受药品试验。
8个月里月均收入2000多元,这样的收入高于周飞之前那个辛苦的证券公司销售工作。
那时他月薪不足2000元,最少的一个月,工资卡上只入账6.98元。
周飞说,多数人在第一次参与药品人体试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做其他工作谋生,但是他们尝到甜头后就不想再卖力工作,不想再看他人脸色。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以此作为跳板,度过经济困难期后离开这个圈子;还有人确实没有能力谋生又不愿乞讨,借此维持生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周飞并不避讳这样形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
他说这群人的任务就是:站着走进来体检表明自己是健康的,然后站着走出去表明一切都没有问题。
招数
“反正你坐火车硬座的时候能做的事情,在试验期间都能做。”
周飞说,参与药品试验时,在体检、吃药、抽血之外,就是与其他受试者一起聊天,以及打扑克、下象棋、看电视,“除了偶尔会头晕、喉咙发干,其他就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周飞是这个圈子里不多的北京本地人。
他“入行”有点偶然:辞职后没有积蓄,又要和朋友去KTV或者出去玩,男子汉的自尊让他难以开口向家人要钱,这时他想到了大学时期没有应聘成功的那次药物试验。
“中学看电视有个节目,就知道了药品试验这个事情,之后一直很好奇。
到读大学终于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体检,可惜因为我抽烟,当时体检没通过。”这个26岁的北京男生家境良好,之前从未遇到过生计问题。
周飞描述他的伙伴们:外地人、年轻、没学历、缺钱。
“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不会珍惜。”就是他自己,在成为职业受试者之后也没攒下多少钱。
据周飞统计,北京地区每年针对一期药物受试者的公开招募有四五十次。
此外北京的受试者也会前往天津等邻近地区。
他们其实也能了解到上海、长沙以及杭州等地的招募信息,但受制于交通成本过高。
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被称为药物临床试验。
它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一期受试者周飞说,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即使有些药物是进行首次人体试验,也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这个年轻人认为,相比食品安全问题,对于制药厂相对严格的卫生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试验药物,没必要太过担心。
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
“比如试验一般都不要吸烟的。
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
周飞专业地解释说,抽烟后留在身体里的尼古丁代谢为可替宁,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过检查。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十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
“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
他说,至于最关键的尿液检验,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
这个过程是:虽然受试者一个接一个上厕所,“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另外一些特别基础性的规定:比如三个月内不能接受其他药物试验,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证解决,“就算被医生护士看到,因为你脸熟,对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周飞认识的一个人,曾经同时参与了三个医院的药物试验。
说这些的时候,周飞的脸上更多流露出深谙此道的得意,毫无烦恼和紧张。
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几个医院参与试验,有经验的受试者绝对不会让医生或护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针眼,“擦点女生的粉底,一切就像新的一样。”
周飞咧嘴笑着说,最大的作弊是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服药后医生会要求受试者张开嘴巴检查。”
周飞觉得,这些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无伤大雅。
而另有一些情况才是整个药品试验中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
分配
某次参与试验,“因为之前参加试验跟医生已经很熟了,我无聊就用他的电脑上网。
结果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块。”
周飞回忆说。
这个情节的意外之处在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已经超出“惯例”---从药厂、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的费用支付及“过滤”链条,有时候并不是秘密。
“比如去年一家三甲医院的试验,药厂给的价钱是每个人9000元;经过医院项目负责人到中介手里,变成6000元;然后中介拿走2000元中介费,到受试者手里就剩下4000元了。”
周飞说,这是一般的分配比例。
“中介起码还做了一些招人的工作,项目方那些人实际上什么都没做就拿了最大一块。”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正常情况下,药厂会向进行试验的医疗机构另外提供研究费用,后者不应对受试者的费用部分再染指。
湖南的受试者刘超对此感受更为直接。
与大部分受试者一样,一个人租住在长沙郊区的刘超,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觉得工作报酬太低,要么觉得工作太累,他的生活开支完全来自参与药品试验获得的补偿。
“每次试验结束后,我们都要在两份类似收据的单子上签字,但两份单子都不能带走。”
这两份单子除了数字不同,其他内容全部一样。
比如他亲历的一次试验,一份单子上写的是5000元,另一份是2500元。
“5000元的是给医生或者项目方负责人看的,而2500元的则由医生的学生或者医生助理收起来。”
参加过接近十次试验的刘超说,这在当地已经成为惯例。
“八九年前受试者拿到的补偿费很高,每次大概三四万元。”
周飞说,当时由于大家对药品试验不太了解而比较恐惧,所以招募受试者非常困难。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试者涌入这个市场,补偿费一路下滑。
他觉得这是市场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手的人肯定不会放过能拿到的利益”。
根据一些受试者的叙述,北京的受试者市场基本已被4家较大的中介垄断,其他人已经很难插足。
“其中有两家是公司运作或者挂靠公司运作,他们的中介费用高一些。
另外两家基本靠与项目负责医生的私人关系而获得机会,由于是个人运作,中介费用相对低一些。”周飞说。
公司化运作似乎显得更加有技术含量。
标签:试药,药厂